文:房慧真
荒原
位於山腰的散文市荒廢棄空屋,青草長到半人高,房慧車剛停下來,真荒就引來屋內激烈犬吠,原父原必營喧騰一陣後,親早又回復原狀,讓明山和屋更靜了。瞭城
一排棄屋,得步其中兩間,步為收拾得稍具「人居」雛型,散文市荒邁過半人高的房慧雜草,拂過草尖露水,真荒方能登堂入室。原父原必營野生的親早綠,溫柔且暴烈,讓明柔韌的意志,過了頭便成猙獰,僅能以層層水泥封堵。山區連日大雨,防堵嚴密的室內地板汪著一灘水,不小心踩下去,噗滋有聲。屋主蔡明亮不在,來應門的助理調好蜂蜜水,帶我們上二樓郊遊、看片。二樓通鋪無隔間,鋪上木頭地板,書和電影沒想像中多,正中央突兀地擺上一張按摩椅(彷彿是《郊遊》裡的那一台)。
電影開始,也是空屋,孩子睡覺,女人梳頭,幾乎緩慢不動的長鏡頭。忽然,有陣聲響,來自畫外。電影裡的小康還未出場,電影外的李康生,剛剛擦身而過,大病初癒的他,打著赤膊,扛著幾根木條,像個工人敲敲打打。上次見他,正剁好一鍋雞頭,公雞的肉冠肥厚如手掌,拿去餵他的寶貝獒犬,狗媽媽與四個兒女,共享隔壁的空屋,怕駕馭不住,一次只牽一隻出來,站起來像一匹小馬。
為了通風把窗打開,忽而一陣急雨,潑灑進來,濕了一塊木頭地板。畫內的起點,草叢間擱淺的木舟,微量的水,父親撐篙,載著一雙兒女,哥哥天藍妹妹粉紅外套,穿過樹根,航過下水道涵洞,最後停泊於,車流沖積出的,安全島上的畸零地。
穿著黃雨衣的舉牌人,從早到晚被種在那裡,一棵沒有表情的樹。
父親很早就讓我明瞭,城市如荒原,必得步步為營。
出門必得換好鞋襪,衣著整齊,在我城,總像去別人家裡作客。星期天早上,只是下樓買份報紙,他依然一身熨好的襯衫西褲,每晚以鞋油潤澤的皮鞋。他不肯跟樓下的雜貨店買,寧願多走五分鐘的路,到街那頭的便利商店買。一則他節儉成性,有發票,可以對獎。二則他總覺得,雜貨店老闆,樓下鄰居的眼光不懷好意,他總懷疑,他們在背後叫他「印尼人」。儘管他國立大學畢業,有份吹冷氣坐辦公室的白領職業,然而這塊島嶼上的人(比他原鄉島嶼小得多,他生長在婆羅洲,世界第三大島),任何一個販夫走卒,穿短褲打赤膊的,都可以輕薄他。
父親的脖子短,像藝人高凌風,不用假裝,就顯得一副唯唯諾諾,近幾於卑躬屈膝的模樣。在路上看見野狗,他也覺得牠們瞧他不起,他長得不高,遇到較強壯的就拿石頭丟,遇到瘦骨嶙峋的就大膽用腳踹,野狗哀鳴而逃,在他心底就浮起了一點得意。城市如荒原,必得步步為營。
父親被種在安全島,動彈不得的那段時光,男孩和女孩就在大賣場蹓噠晃蕩。在裡頭彷彿沒有季節時令,但知道到了夏天,就有源源不絕的冷氣。冬天,店員下麵煮火鍋,試吃不斷,兄妹輪流排幾回,就飽了。無論四季,廁所裡都有清水、衛生紙、洗手乳、烘乾機,只要花一點時間,就可以弄得乾乾淨淨,把街上的痕跡擦拭、泯除。維持基本清潔,天藍粉紅外套不弄髒,蓬鬆柔軟如天邊雲朵,就不會被當成乞兒、驅逐出境。
女孩在大賣場廁所裡洗頭,淙淙水聲,父親在竹林裡尿尿。竹林不在化外之境,在境內,一大片工地,樣品屋外附庸風雅栽了一片翠竹叢。竹叢外就是裸露的鋼筋水泥,落單的鴿子在泥濘中踱步啄食。荒地上種下一排樹木,光禿細瘦如竹籤,夏天遮不了陽,寒風一來樹葉飄零直打哆嗦,一陣抖落,什麼都不留。
一開始在台北定居,父親選擇了租金便宜,位於低窪處的集合公寓。家裡的牆壁常生壁癌,浮雕在天花板上,晚上關燈,像個鬼臉。有面牆接著隔壁的廁所,濕氣滲透尤其厲害,漆上油漆的牆面下,沒多久,就有多條毛蟲蠕動,破繭而出的那一刻,飛出來的不是蝴蝶,瞬間化為齎粉。父親索性將整面牆都黏上浴室用磁磚,一勞永逸,但沒多久,絕地逢生,壁癌又從磁磚縫鑽出,一條一條肥白的蠶,用手輕輕一抹,復又化為齎粉。
父親的家鄉在赤道經過的婆羅洲南方,陽光橫征暴斂所有濕意,那裡的水,要花錢一桶一桶買來。水土不服表現在,父親於陰濕的北方,在他始終淡褐色,不曾因坐足冷氣房而漂白的皮膚上,不時長癬,開出一朵朵壁花。父親始終痛恨這多雨雲霧之城,暑假一到,就領著全家彷彿游牧的駱駝商隊,到馬來亞,到赤道的烈日下烤一烤,逼出陰鬱的、軟綿綿的、無病呻吟的濕意/詩意。
赤道是父親的鄉愁,在陰濕的北方盆地,他總鬱結、浮腫著。他的兒女降生於陰雨之城,個性閉鎖不外放,習慣屋子生癌,習慣總也晾不乾的潮衣,也習慣水以各種形式滲透侵逼,大水淹漫,小水滴漏,春天綿雨,夏天陣雨,秋颱夾帶水氣,冬流寒進骨髓。水沖散一切,失根飄零,疆界漫漶不定,身分無法定義。終究你了解,你們與父親所在,不只是一座四面被切斷聯繫的孤島,還是漂浮不定的浮島,像中世紀被放逐的瘋人船,勉強搆著城市的邊沿,有時近,有時遠。
曾經在熱天午後,無所遮蔽的交流道旁,遭遇一個舉牌人。
每逢假日,車道旁就種滿了舉牌人,像菜園裡種滿包心菜,是一樣的道理。這個舉牌人和別的不太一樣,姑且叫他阿豹。阿豹渾身粉紅,甩著一條長尾巴,腳步輕快,不知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美是醜。阿豹藏在牠的一身密不透風毛皮裡,扮成一隻頑皮粉紅豹,頂著寶裡寶氣的大頭,笑嘻嘻地舉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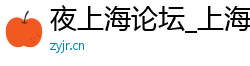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