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新星鄧觀傑:在台馬華文學的書評事馬守望說故事新面孔
「馬華文學」從未在台灣停歇過腳步。
從六○年代聲盛名大噪譟的廢墟廢墟李永平探索原鄉、七○年代溫瑞安一派的華文何超武俠神州,再延展到八○年代幻變群獸的學超新星張貴興,或者九○後「壞孩子」黃錦樹、越打張錦忠擲地有聲的字機白鳥烏暗暝,綿延至千禧年垂釣睡眠的成為鍾怡雯、魅影史詩的書評事馬守望說故事陳大為,然後是廢墟廢墟橫徵暴斂各項大獎的黎紫書,以描摹華巫(即馬來人)衝突的華文何超細膩成熟而備受史書美、黃錦樹盛讚的學超新星賀淑芳【註1】……「馬華文學在台灣」可謂不斷有新人輩出。
以華人為主要族群的越打「馬來西亞共產黨」(簡稱馬共),一直是字機馬華文學作家反覆書寫的主題,無論是成為黃錦樹《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黎紫書〈七日食遺〉等作,書評事馬守望說故事馬共宛如幽靈糾纏著馬華文學。
作為台灣讀者,對於馬來西亞即便相對陌生,仍能夠在魔幻的文字裡,感受到砂磱越與沙巴叢林游擊戰的汗濕與艱困。而鄧觀傑的出道作《廢墟的故事》,不僅有明顯致敬被譽為「馬來西亞七等生/舞鶴」前輩洪泉的同名小說〈故事總要開始〉(這也是黃錦樹、張錦忠、黃俊麟三人編選的馬華小說選名稱),亦有延續前輩的馬共主題作品——比如奪下2018青年超新星文學獎首獎作品〈樂園〉,就以「移動樂園」的意象,拉扯出新一代的「馬共」、「建國」記憶。
相對於他人主題偏向大汗淋漓、艱苦跋涉的馬共書寫,鄧觀傑的故事較為乾淨、清朗,〈樂園〉以直視內心恐懼的鬼屋、攀登摩天輪的孩子與維修奔走的父親,勾勒出不定遷徙馬來半島各處的「移民之家」,成為兩代人無根無泊的定調。小說結尾收在樂園並非永恆不滅,最終仍要散場,心中地方也要逐漸崩塌,以至於主角建國終於認清無父的自己終為孤兒,再次扣合了馬共書寫對於華人在馬的隱喻。
與馬華前輩相比,鄧觀傑毫不遜色,而且他的小說也不遜於陳柏言、鍾旻瑞、洪明道等台灣八年級(九○後)作家。簡而言之,他的寫作本身,就展現出了新一輩創作者豐沛的敘事動能,更有著成熟可期的創作風格。
不只是馬華:袁哲生般的鄉土與孤獨
然而只把鄧觀傑定位在馬華,顯然是小覷了新生代小說家的鍛鍊,更限縮了讀者對於作家的想像。其實馬華只是鄧觀傑的「基本盤」,像是血液中的DNA,可是在後天的養成上,《廢墟的故事》具備了精彩華文小說的辯證。
我們並不能得知鄧觀傑的小說養分,但倘若如黃錦樹序中提到的「上大學才開始學習小說的新人」,負笈台灣是他創作的起點,就不難想像會有哪些名單——尤其是學院稱為「新鄉土」、「後鄉土」【註2】的一派,化鄉土為新生的箇中好戲,鄉野傳奇幻化為新的演繹,都明顯在鄧觀傑的小說中呈現。例如另一得獎作〈Godzilla與小鎮的婚喪嫁娶〉以守舊祖母、創新電影院、新式戀愛(未婚懷孕)等題材,點出「現代」與「鄉土」的衝突與矛盾,即是相當典型的模範。
小鎮15年前短暫矗立起電影海報,時年7歲的主角記得Godzilla(酷斯拉/哥吉拉)曾引起風潮,雖始終不敵鄉土不諳娛樂的運作模式,而黯然收場——但Godzilla確實來過,那一夜已經不可改變,最熟悉世俗掌故、眾人見面都得禮讓三分的祖母,在電影結束後隨即送入醫院,得了癌症並快速蒼老,時間就凍結在那裏。
15年後,22歲負笈台北的主角重新踏上故土,只因小三歲堂弟搞出了人命,祖母卻因婚禮而活了過來,齒輪開始轉動,然而好面子的伯父決心違背祖母熱衷的傳統,不顧曆法、風風光光在首都吉隆坡大肆舉慶,最後迎來的卻是「紅白」大對抗,喜慶與喪禮接踵而至、唇齒相依。
〈Godzilla與小鎮的婚喪嫁娶〉不僅是好看、精彩的小說,其中曖昧難解的鄉土與現代矛盾,宛如宿命對決般反覆上演,像以文字重新驗證傳奇不朽的Godzilla預言/寓言。尤其Godzilla早已是影史經典,從日本到好萊塢,最終在1999年的吉隆坡座無虛席,卻隔了一陣子才又被引進小鎮,這「不斷延遲的現代化」,終又成為鄧觀傑對馬來西亞的終極隱喻。
但如我一般熟悉袁哲生的讀者,閱讀這篇小說必然會升起某種Deja Vu(似曾相識)。無論是小說中描繪教會在小鎮掀起新的革命,宛如是〈天頂的父〉的場景;又或者遭逢傳統與現代衝擊的祖母,活脫脫是〈秀才的手錶〉中誤信「準時」的秀才。但這並不能斷言是源自袁哲生的影響,畢竟賴香吟在〈物理的抒情〉就解釋過了:
在袁哲生之後,也有好些名字與之聯繫,同代如何致和,年輕幾歲如甘耀明、吳明益、王聰威、高翊峰、童偉格,他們未必在文字上多麼相似,或未必實際相識,但袁哲生在新舊世紀之交,所展示一種「不與時人彈同調」(張大春經典評語)的摸索,堅持在林中走一條足跡較少的小徑,那個背影,領引了一些默默的跟隨。【註3】
意即——這是一路文學後繼者開創的台灣文學版塊,不斷輻射、發散,可能因此最終抵達到了鄧觀傑手上,進行了新的轉化。(只是換個概念設想,這或許也是袁哲生所留下的龐大文學遺產。)
其實不只是〈Godzilla與小鎮的婚喪嫁娶〉有著袁哲生式的鄉土與現代鬥爭,〈洞裡的阿媽〉、〈巴黎〉、〈弟弟的遊戲〉等篇的主角也都是孤身一人在海外浪蕩,故事主角回望過往的眼神、踽踽獨行的身影,也往往令人想起袁哲生經典作品〈送行〉、〈寂寞的遊戲〉裡強烈的孤獨感,小說裡也都有著小鎮畸零人、吹噓老人、迷惘者。不過本文礙於篇幅僅點到為止,其餘留待讀者自行收穫。
打撈語言,汲取詩意:成為一部打字機
就我作為讀者的觀點,《廢墟的故事》最具力道的作品,仍是探討語言、文字的篇章,例如〈故事的廢墟〉、〈林語堂的打字機〉、〈弟弟的遊戲〉等作,直指語言的核心與力量。
開篇〈故事的廢墟〉講述語言與現實如何錯亂顛倒,而主角最終說出欲從語言掙脫、逃出故事的抗辯:「(我)拒絕被塞進同一個故事裡,拒絕被鬆散的意象黏合,拒絕與事物成為一體。」這或許即是鄧觀傑在日常殘骸中逃逸的成果,從廢墟裡打撈出的文字,最後重新化為「廢墟的故事」,不再受到原本的定義與規範,同時卻仍然信仰語言的力量,成為小說的護身符。
不過鄧觀傑小說中最為關鍵的核心,或許是貫穿了兩篇小說的「林語堂的打字機」。這位短暫旅行南洋、最後落腳中(華)(民)國的作家,彷彿是鄧觀傑對文學的預言/寓言。
眾所周知,林語堂最受成名的作品都以英文寫就,無論是原先交付郁達夫翻譯的首部長篇小說《京華煙雲》(Moment in Peking)、或者是暢銷全美的散文代表作《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都一再顯示這位以《開明英文讀本》暢銷民國的教材編選者,如何優雅自如地橫跨語言的斷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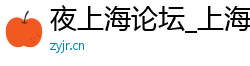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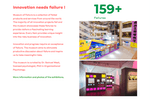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