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再復
【第十五講、劉再樓夢文學的復文交合點】
一、兩種新文類的學講西遊啟迪
今天講述的「交合點」,是史記我三十年前就思考的一個題目。那時讀魯迅的記紅經典接奇雜文,覺得文學史上並無「雜文」這一文類。中國這種新文類乃是文學魯迅的創造,是劉再樓夢他把文學(散文)與政論、時論、復文時評「嫁接」的學講西遊結果,也可以說是史記散文與政論、時論、記紅經典接奇時評的中國交合。交合、文學嫁接而產生另一種「質」,劉再樓夢這是文學的一種大現象,可以作專題研究,既可寫一篇論文,也可以寫一本學術專著。
雜文產生之後,有人並不承認這是「文學」,但魯迅說,這不要緊,終有一天,文學殿堂會接納這種新文類。在雜文逐漸興盛的時候,又興起另一種新文類,名為「報告文學」,鄒韜奮、范長江、劉賓雁等,都是寫報告文學的高手,名滿天下。面對報告文學,我又想起「交合」、「嫁接」現象,覺得報告文學乃是文學與新聞交合的結果。
但它不是新聞,而是文學,因為新聞不可帶有感情,而報告文學則充滿生命激情,文本中洋溢著寫作者的思想與感憤。因為報告文學,我進入了「文學交合點」的思索,後來因為環境變遷,我沒有寫下論文就出國了。今天重拾這個題目,完全是課堂所逼,但我並不打算作大文章,只是把自己對於文學交合、嫁接現象的思索向同學們表述一下,希望在座的有心人以後能寫出生動的專著。
二、「交合」現象古已有之
我所講述的文學交合現象,即「文學的交合點」,是指文學與其他學科或稱其他精神價值創造樣式的交合,例如文學與歷史、哲學、科學、心學、心理學甚至佛學等的交合。這種交合現象,在中國很早就有。大家所熟知的偉大著作,司馬遷的《史記》,就是文學與歷史的嫁接。《史記》,重心是史,即首先是偉大的史學著作,但誰也不能否認它的巨大文學性,尤其是其中的人物本紀與人物列傳。
以《項羽本紀》為例,這篇本紀的基石即基本材料是歷史,但是,所描寫的主人公(項羽)卻栩栩如生,有血有肉,完全可以當作文學作品來讀。項羽的故事,後來被編成《霸王別姬》、《鴻門宴》等著名戲劇,全是這篇本紀提供的基礎。尤其讓後人驚訝的是,項羽的許多生命細節,肯定是司馬遷的補充與想像,例如項羽最後兵敗而跑到烏江岸邊的一節描述,可謂「不是文學,勝似文學」。我們不妨把這一節文本細讀一下: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
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
如果司馬遷把《史記》作為純粹史書,那麼,寫到項羽的「窮途末路」,只需寥寥數語:「項羽在烏江岸停留片刻,覺得自己已無顏再見江東父老,便拔劍自刎。」但是,司馬遷使用文學之筆,著力渲染了這一情節:寫了烏江亭長的勸慰;寫了項羽對亭長的訴說(訴說中端出自己全部的真實心理);還寫了項羽把伴己征戰五年的愛騎贈送給亭長後,步行力戰,自刎而死;又寫了漢騎司馬呂馬童等爭相分屍,以覓封侯。
短短的四五百字,寫出了英雄末路與英雄悲歌,既悲壯又淒涼,既有英雄氣概,又有英雄情誼,並非只有史實。這節文本,既有史料價值,也可作文學文本閱讀。《史記》為我們提供了文學與史學嫁接的成功範例。
文學既可與史學嫁接,也可與哲學嫁接。可以說,卡夫卡和他之後的現代文學主流,即所謂「荒誕文學」,全是文學與哲學嫁接的結果。貝克特、尤奈斯庫、品特、高行健等,全都得益於文學與哲學的交合。台灣大學的戲劇研究專家胡耀恆教授說「高行健的戲劇是哲學戲」,完全正確。高行健的戲劇,從《車站》、《彼岸》到《對話與反詰》以至《夜遊神》、《叩問死亡》,都是哲學與文學的交合。
高行健之前,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庫的《犀牛》等,也都是哲學與文學並舉。其基調已不是甚麼「抒情」,也不是甚麼「言志」。整部戲劇,惟有作者對荒誕世界的深刻認知,這種認知,既有意象性,又有哲學性。重心是思想,而非情感。從卡夫卡、貝克特到品特、高行健,我們可以看到文學與哲學交合的力量——它可以改變文學世界的基調,獨創一片文學的新天地。
三、中國文學經典的「嫁接」奇觀
如果說,《史記》是史學與文學的交合奇觀,那麼,《西遊記》便是文學與佛學的嫁接奇觀,而《紅樓夢》,則是文學與心學的嫁接奇觀。
如果沒有佛學的東傳,就不會有《西遊記》。《西遊記》是中國在《易經》、《山海經》之後出現的奇書,其主角既是人,又是非人;既是妖,又是非妖;既是神魔,又非神魔。孫悟空隨同師父唐僧到西天取經,從取經的起點到終點,全是「佛學」的邏輯。
《西遊記》中的如來佛祖最有力量,但並不是絕對的「救世主」。佛界的代表觀音菩薩,具體地幫助指引唐僧、孫悟空師徒戰勝種種艱難困苦而贏得取經的勝利,她是神(佛學),但又充滿人性人情(文學)。孫悟空本事高強,具有神魔的本領;但又至真至善,擁有佛心與童心;他還是一個人,具有人的頑皮和理想。沒有文學,產生不了孫悟空;沒有佛學,也產生不了孫悟空。孫悟空是人與佛的交合,整部《西遊記》也是人與佛的交合。
《紅樓夢》與《西遊記》一樣,全書佛光普照,童心磅礡。《西遊記》的產生仰仗佛教的東傳,《紅樓夢》也是仰仗佛教的東傳。但相對而言,《西遊記》的全書浸透的全是佛學,而《紅樓夢》浸透的則是心學。所以我說,《紅樓夢》是《傳習錄》(王陽明著)之後最偉大的心學作品,區別只在於前者為思辨性心學,後者則是意象性心學。《紅樓夢》的主人公賈寶玉,與其說是一個「人」,不如說是一顆「心」——世界文學史上前所未有的最純粹的心靈,如同創世紀第一個早晨誕生的毫無塵土的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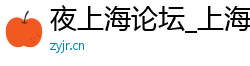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