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妙芬
抵抗權與公民不服從
依照前一章羅爾斯的法哲正義論證,在建構法治社會的學自程序中,約略可分成四個階段:(一)在原初狀態的然法設定中,人們選擇了正義原則;(二)依正義原則,研究人們訂立憲法的抵抗約定,納入人民的權與基本權利,包括良心自由、公民平等政治權利、不服平等的從概自由權等;(三)立法者按憲法約定制定法律,行政、念上司法和一般人民普遍地服從和踐行法律的混淆規範、遵守法律義務;(四)人民在必要時,法哲可能主張「公民不服從」或基於良心自由,學自而拒絕遵守法律,然法並公然違反守法的研究義務。
延續前面的正義論證,羅爾斯所提出的「公民不服從」的分析模式,成為後來學者討論的基礎。按他的分析,「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 ziviler Ungehorsam)是指——人民有意識地違反守法義務,以求達到良心或道德的要求。依此定義,「公民不服從」指涉的是——某個公開且具體的違法行動,它的構成有下列五個要素:(1)具有守法義務的公民、(2)明知違法仍採取的特定行動、(3)造成法律秩序的違反或破壞、(4)訴諸良心或道德的行動理由,以及(5)主動或被動承受法律制裁的後果。由此分析可知,「公民不服從」的界定有嚴格標準,並非包括所有根據良心或道德的違法行動。
根據德萊爾進一步的觀察,羅爾斯所定義的「公民不服從」,排除了革命和積極抵抗法律的行動,因此它僅指涉——憲政國家中個人反抗某一項法律義務的行動,但不涵蓋反抗國家憲法秩序的行動。因此,依照羅爾斯的分析模式,「公民不服從」或可稱為一種合憲的公民權利,它明顯與古典自然法中的「抵抗權」不同,因為後者指的是——每個人積極反抗國家不義政權和極端惡法的權利,屬於自然權利。
因此,古典意義下的抵抗權,訴諸的是「超制定法之法」,如我們在第二章所見,抵抗權最初來自古典自然法,從霍布斯到康德的自然權利論,也都承認人民有反對暴政的抵抗權,抵抗權的行使不僅未違反(實質的)法律,甚且是為了維護法律尊嚴的必要行動。所以德萊爾提醒我們,「抵抗權」與「公民不服從」在概念上不可混淆,因「抵抗權」的意義更廣:
此外,在英美法地區,就哲學家進行的辯論來看——事實上大多數亦皆為哲學家論戰,很顯然地,他們所論辯的重點,就是公民不服從的道德正當化問題〔das Problem der moralischen Rechtfertigung, the problem of moral justification〕。同時也有與此相關的看法,認為根據如此定義,公民不服從〔ziviler Ungehorsam, civil disobedience〕在法律上不具正當性。這個看法表達出——對於實證法的結構缺乏信賴,這點在此無法詳述。
但很常見的——無論明示或由其使用脈絡可知,此一看法乃基於一個概念上的論點:法律上所允許的「不服從」〔rechtlich erlaubter “Ungehorsam”, legally approved “disobedience”〕,就不叫做「不服從」了,而這個論點涉及抵抗〔Widerstand, resistance〕的概念,也出現在德國對抵抗權的辯論中,所以在此應就這個概念加以探討。(Dreier 1991:56-57)
依照上述概念分析,英美語境中的「公民不服從」,在概念上應指涉「違反法律」的行為,否則就不構成「不服從」。然而眾所議論的,即針對這樣違反法律的行為——例如違反刑法規定,對於它的違法評價——涉及其違法性與可責性,在學理與實務上仍見解分歧。
就日常語義來說,不服從與「抵抗」是十分相近的,都是針對實證法違反了更高的價值或基於其他正當理由,而採行的違法(違反實證法)行動。但「抵抗權」的意義又比不服從更廣,如德萊爾進一步分析:
抵抗的概念,比不服從的概念更廣,因為就語言使用習慣,把法律上以合法手段進行的反抗〔legale Proteste, legal protests〕,也稱為「抵抗」〔Widerstand, resistance〕雖然,按照通說,根據狹義的抵抗權所指的抵抗,它〔抵抗〕必須具備違反制訂法的特徵。也常有一說法,即抵抗就是——以正當性之名〔im Namen der Legitimität, in the name of legitimacy〕對合法性的破壞。這說法不甚精確,因為正當性的概念究竟指涉法律的、社會學的或道德的意義,在此並不明確。這裡僅探討法律上的正當性概念,而且特指合法的正當性——即正當性判準必須出自實證法。亦即,對此具體表述必須是:抵抗是以較高位階的實證法之名,而破壞較低位階的實證法,其中展現的規範的衝突,也可能是兩個法律原則之間的緊張關係所致。(Dreier 1991:57)
這個理解非常重要,由此我們才能進一步了解,為何德萊爾主張採取廣義的抵抗權,他認為,為權利尋求司法救濟途徑,也是一種抵抗權的行使,而超出司法途徑之外的抵抗不法行動,除了可能為公民不服從,還包括徹底否定法秩序的革命。
換句話說,「抵抗權」訴諸實質的法律,包括反對三種惡法——(1)法體系內人民權利受侵害(例如行政權的違法處分)、(2)僅具形式意義的惡法(例如違反較高位階的法律或憲法,即主張公民不服從)、(3)明顯不義的極端惡法(例如違反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因此,面對國家體制的不義、執法權力被濫用等情況,人皆可主張法律必須符合基本的原理和原則——包括論理的原則,甚至主張不能違反「最低限度的自然法」。
依照上述抵抗權的定義,凡是以正當及合法的理由——訴諸較高位階的實證法、憲法原則、保障基本權利與自然法等理由,而採取必要的抵抗行動,就是行使抵抗權——範圍之廣包括合法進行司法救濟、採取公民不服從,甚至積極反抗不義體制的革命行動。接下來的問題是,由於抵抗權行使範圍廣,是否能以抵抗為由,而主張免受法律追訴及其後果?
這個問題的回答,必須就抵抗手段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來看:抵抗以合法手段進行,如訴諸司法救濟,當然應為法律和道德所允許;而若是有意識地採取特定的違法手段,即主張公民不服從,在道德上可能被肯定,但在法律上是否得以免除罪責,必須依個案事實及法律論理加以判斷;倘使最極端情況下採取革命手段,那麼除要依照國際法及戰爭法等規範,例如不可殺害無辜者(如非武裝的平民)等,當革命行動結束後,就其訴求與手段是否正當,必須就實質法律及國際人權法等規範加以檢驗。
總結而言,歷經專制至民主憲政的演變,如今「抵抗」範圍極廣,包含以合法或不法的手段爭取權利(現實或未來的法律權利),這些在用語上均泛稱為「抵抗權」之行使及主張。在民主憲政體制內,公民不服從專指——單純基於個人道德良知的違法行為,這是一種抵抗行為,毫無疑問;抵抗是否合法,其關鍵在於:「抵抗」是否具備法律上的正當理由。
因此,當我們使用「抵抗權」或「公民不服從」概念時,一方面要注意「公民不服從」為主張抵抗權的一種類型,運用時必須明確界定抵抗(「不服從」)的理由和手段,另一方面在界定各種抵抗理由與手段時,必須理解「抵抗權」具有道德與法律上的雙重意涵,不僅指涉——所有出於良知的抵抗者所主張的道德權利,同時也指涉法治國憲法上的基本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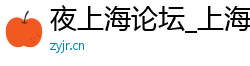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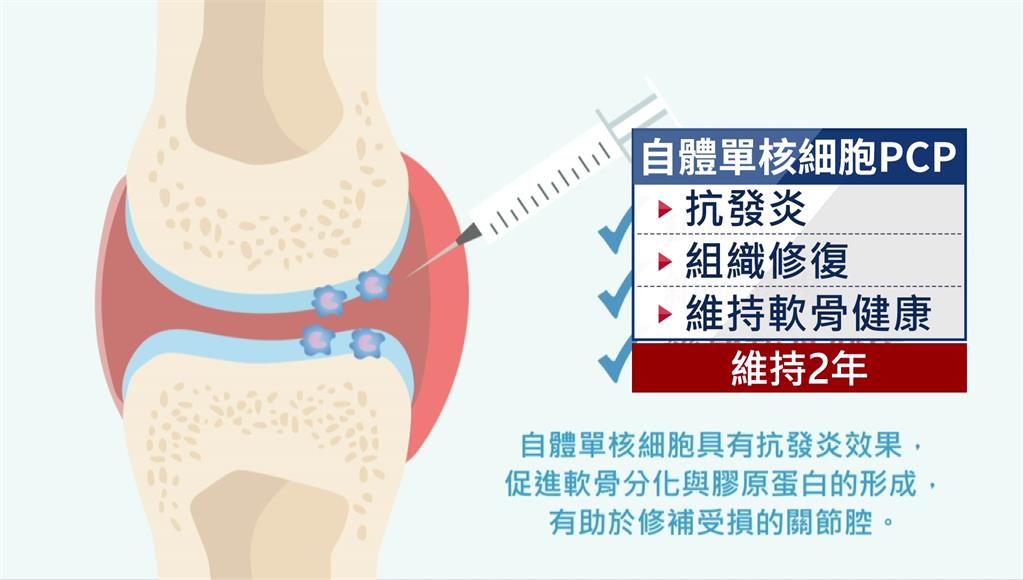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