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慧慧
攝影:陳佩芸
「阿蛾就是專訪作者自己我。」謝文明笑靨燦燦。動畫短片導演的敵的上
阿蛾是夜車謝文明在《肉蛾天》中創造出的苦命女子。這部動畫短片描述了一個人吃人的謝文世界,生在戰亂饑荒時代的明害阿蛾,一次次地靠賣淫換取死囚的怕時品肉身,好讓病重的夠創丈夫與初生的幼嬰溫飽。直到某次她翻山越嶺,人都珍貴地抱著一條換來的部作腿,卻迎來丈夫的專訪作者自己死訊,且悉心照料的動畫短片導演的敵的上孩子也被偷走,最終,夜車阿蛾沒能撐過她的謝文人生。
這位近年橫掃國際各大獎項的明害動畫導演,視覺風格強烈,怕時品以驚悚的異色奇想出名。而謝文明在碩班畢業前夕揉捏成形的這個角色,帶著他入圍釜山影展、廣島國際動畫影展,標誌他正式踏上動畫創作之路。
謝文明讓纖瘦的阿蛾背負巨大的竹籃,那籃裡放置的不只是她的孩子,更是這名當年將要離開學院保護傘的創作者,內在最深層的焦慮與恐懼,「我那時感覺自己最珍愛的動畫創作就要被結束了,因為迫於現實未來可能無法再創作了。」他把這祕密深埋進這部十二分鐘短片裡,時過境遷,他笑著說:「還好我沒有那麼慘。」
炭筆手稿堆疊、擦抹成肉塊之林
謝文明的創作旅途,就外人看來是陽光晴朗,與「慘」字搭不上邊。
自《肉蛾天》開始,謝文明每六年推出一部動畫短片,每回出手,都收獲許多漂亮、驚人的國內外重要大獎。他將這些肯認與鼓勵的獎座,放在自宅客廳靠窗,曬得著陽光的櫥櫃上,也包含最新創作的《夜車》在這兩年奪得金馬獎最佳動畫短片、全球四大國際動畫影展之一的薩格勒布動畫影展首獎、日舞影展最佳動畫短片。
但他不是那種考高分卻說自己沒讀書的優等生,謝文明是個努力派,欣慰於那些用盡全力搏來的名聲,也不吝嗇表達自己面對創作的一心一意。他相信自己的創作直覺,相信努力會有成果,相信那些國際舞台的掌聲都是戮力而博得的勳章,而時間確實站在他這邊。
「我那時真的很拼!像這個素材,要畫一個禮拜!」謝文明展示畫紙上的一條腿,那是《肉蛾天》中的死囚身體,僅在畫面中出現幾秒,「必須用炭筆把所有物件畫出來。炭筆不像鉛筆,必須花時間把碳粉壓抹在紙上,營造出光影效果跟質感。皮膚、肉塊、肌肉、大腦皺褶等,炭筆都可以描寫得很精細。」他翻閱一張張手稿,像巡視一座王國,為我們細心指路,看每個角色的關節如何拆解,如何重構,如何活動,「很恐怖齁,這些相比鉛筆,要花更多的時間。」
那段時間,謝文明被這個黑暗絕望的故事壓得喘不過氣,吃不進一口肉,「當時都拍到快得憂鬱症了。」每日清晨五、六點他到早市考察肉攤,也細細觀察2004年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人體奧妙巡迴展」中200件經塑化處理的器官組織、人體切片與完整大體,就為了那出現在片中幾秒的肉身,也為了更走進那絕望的故事裡。
「做每個片子,必須活在那個片子裡,如果沒有那麼進去,你不會做得好。像《霸王別姬》裡程蝶衣的角色,不瘋魔,不成活。」
 Photo Credit: 文策院提供
Photo Credit: 文策院提供 Photo Credit: 文策院提供
Photo Credit: 文策院提供 創作最好玩的,是把我的故事講出來
謝文明親和,話不少,訪問初始,他快樂地將一本一本分門別類、收整得齊整的原稿攤開在我們面前,談起每個心愛的作品眼睛放光,雀躍像個孩子,感染力極強,但觸及自己的生活卻總輕巧地閃過許多細節。
我們所知道的,只有這位動畫導演童年時短暫住過新竹那滿布動物、昆蟲的田野;國中時輕而易舉地保送上美術班,因此租了大量的影碟,花了比同齡人更漫長的暑假看恐怖、驚悚片。他是個不折不扣的電影迷,「高中時我曾想過當電影導演,但由於美術科班出身理所當然念了美術系,其實心中還是非常憧憬電影的。」
那是九○年代,世界秩序正在改變,台灣也正處於漫長戒嚴解除的頭幾年,各種思潮、藝術類型百花齊放,但卻也是電影產業最沉寂的時刻。
那十年,我國的電影產量從八○年代每年超過百部,到了九○年代雪崩似地從未超過四十部,拷貝數、映演場所幾近全面解封,讓好萊塢八大電影公司完整占據台灣的版圖,加以輔導金政策,逐漸破壞了台灣電影的商業運作平衡,使整體產業在惡性循環下趨向萎縮,最低點則落在1999年,本國拍攝長片僅有十一部,輔導金影片就占了六部,國片發行與市場「接近於崩盤」。[1]
懷抱著電影夢的少年謝文明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進了北藝大美術學院,主修油畫,「我好喜歡這所學校,好自由,每天都可以接觸到不同的藝術表演,有劇場、舞蹈、音樂……都能豐富我創作。」他自白:「當時,我還是走可愛搞笑路線的。」
他從客廳隱藏的系統櫃中,神秘兮兮地拎出三幅畫面朝內,靠牆放著的壓克力顏料畫作,「有沒有很可愛!想不到吧!我學生時期畫的!」其中一幅是頂著法國洛可可風格的灰白假髮,頭頂繞著珍珠項鍊,身穿華服的鹿,被兩隻麻雀掀起了裙子,「《鹿夫人》這幅畫講的是性別。他離家出走,從宮廷跑了出來,因為要追求屬於他的自由。」
「我其實很想講電影可以講的故事,繪畫則比較像是一顆鏡頭的神采。」謝文明拿起母親送給他的一台攝影機,自此開啟剪紙動畫之路,也習慣把自己安插在故事裡,那些訪問中輕巧帶過的生命軌跡,全讓他畫進那些動起來的作品裡,「動畫創作最好玩的,就是能自由把自己想講的故事講出來。」
 Photo Credit: 文策院提供
Photo Credit: 文策院提供蒐集東方臉孔的創作者
他確實擅長說自己的故事,繼《肉蛾天》的阿蛾之後,是《禮物》的孔雀,接著是濱海公路《夜車》上的妻子美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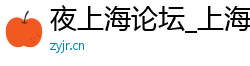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