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乏筆(Fabian Heubel)
哲學生命與工夫論的修養性戀現代化
一、試論「同性戀工夫」
晚期傅柯在說明現代性與工夫論的與批言同關係時特別提及兩個例子:19世紀法國詩人波特萊爾所代表的「浪蕩子工夫主義」,以及20世紀的判傅「同性戀工夫」(ascèse homosexuelle)。這兩種「界限經驗」成為了激烈爭論的工夫工焦點。本章由「同性戀工夫」一詞出發,當代的重反省「工夫」(ascèse)的實踐現代化,進則探討傅柯對古代歐洲哲學與基督教的修養性戀比較研究,尤其是與批言同哲學工夫與基督工夫的對比。
無疑,判傅傅柯實驗性地使用「工夫」的工夫工方式,乃從同性戀文化的當代的重經驗中獲得關鍵啟發。但同時,實踐他也試圖將修養論的修養性戀主題從「性」中獨立出來。因此,與批言同思考同性戀工夫,判傅不僅有助於理解傅柯修養論的批判意涵,亦可藉此反思「工夫論」的現代化問題。
在法語中,使用ascèse一詞,容易引起許多負面的歷史聯想,如基督教以禁欲為目的的苦行傳統(在漢語的語境中,「工夫」一詞也可能引起相似的反應,例如讓人想起宋明儒學「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嚴格主義)。然而,傅柯總是要擺脫「工夫」無形的禁欲陰影,突顯其當代色彩。在一篇訪談中,他界定ascèse如下:
棄絕快感的工夫主義(ascétisme)已名聲敗壞,但工夫(ascèse)是另一種東西:是進行自我在自我身上的工作,為了轉化自身,或是為了顯現那一種我們絕不可能達到的自我。這不就是我們今天的問題嗎?工夫主義已經告辭了。我們的任務乃在於推動一種同性戀工夫,其將會使我們在我們自身上工作,並且發明(我不是說發現)一種尚不太可能的存在方式。
為了闡明工夫論的批判潛力,必須暫時擱置禁欲主義的表淺聯想,融入傅柯對此概念的特殊使用。就此,哈普林(David Halperin)指出:「無論傅柯工夫概念聽起來多麼疑似天主教,他所描繪的現代例子卻都是全然世俗化的。」傅柯不僅強調,工夫的基本意涵與宗教工夫有所區別,也反對將工夫化約為「精神習練」(exercises spirituels)。他避免正面使用「精神習練」的語彙,也不回應20世紀如何實踐精神習練的問題,反而將工夫視為貫串精神經驗與身體經驗的美學實踐。如此,他擺脫宗教式的、偏重精神修養的工夫論。
在此情況下,部分傅柯研究者,尤其在面對某些性實踐如S/M(愉虐戀)或拳交時,「精神習練」一詞顯得不合適。可以確定的是,傅柯自覺地將身體及感性的強度經驗納入「修養」的領域。所浮現的新工夫論以創造性為核心。創造性具有精神向度,但卻無法化約為精神性。「創意工夫」的構想透過界限經驗而連結工夫與美學。在其中,自我要擺脫自己以轉化成「新自我」。對此,哈普林指出:
工夫(ascesis)的現代版本或許在主題上或在實質內容上與古代工夫有所對立,但兩者在結構上確有所相似。究竟連接現代與古代的工夫形式,乃是一種超越自我的自我修養技術(technique of cultivating a self that transcends the self) ,即修養一種激進非人格的自我(radically impersonal self)可當作自我轉化的媒介,因為他自身是虛無的(nothing in itself),因而便占有一種目前仍未成形的新自我的位置。
將「工夫」描寫為超越自我的修養技術,不僅意味著古今在結構上的相似,更具有跨文化的意義。就自我創造的觀念而言,「基進非人格自我」的說法,可算恰當的描寫。但值得注意的是,阿多意義下的古代精神習練與上述的現象不同,因為精神習練是指一種擺脫現有自我以發現真我的過程。哈普林將同性戀理解為精神習練時,並未意識到,傅柯與阿多在解釋古代工夫方面彰顯了不同的哲學範式。實際上,哈普林所提倡的現代工夫與阿多意義下的精神習練難以調和,反而接近傅柯將自我轉化視為自我創造的趨向:以自我越界的「界限態度」作為自我創造的內在動力。
米勒(James Miller)撰寫的傅柯傳透過界限經驗和越界的主題,連結了傅柯的理論與生活。本章焦點不在討論米勒的論著,但要強調的是,這本書將傅柯的思想與生活視為一種「哲學的生命」。哈普林強調,傅柯的生命是為連接批判分析與政治運動的「強而有力的典範」。因此,討論生活與思想的關係,並不等於窺視傅柯私人生活。
哈普林批評米勒說, 他從「個人病理學」而非從「抵抗技術」(techniques of resistance)的角度解釋傅柯的性實踐,將規範權力和正常化的邏輯強加到他身上。而這正是傅柯一輩子所要反抗的。米勒所勾勒的「越界敘述」(narrative of transgression)確實使得性實踐的政治意涵在窺探傅柯個人生活的精神病理學中消聲匿跡,並且進行基督教式的主體詮釋學,即要在自我最隱密的欲望衝動中,辨認「主體的真理」。
依米勒的研究角度,傅柯對工夫論的實驗性研究,容易被視為偏差、變態、不正常甚至病態,進而被歸類為非理性。儘管米勒對界限經驗的強調引起了學界的激烈反駁,但不應因此而忽視界限概念和越界態度所包含的哲學問題:為何現代創造性的發展動力與越界的邏輯不可分?刻板地將現代與後現代切割開來,便在現代性的理性與後現代的理性批判之間造成簡單對立。然而,有關現代性的思考,一旦從理性移轉到創造性(而且將理性理解為創造性內部的結構化作用),過去被現代理性所排除之物,就要看成現代性的組成部分。
例如,薩德(Marquis de Sade)著作中的「性過度」或納粹集中營的死亡工業,都不應該排除在現代性之外。理性與反理性在現代性的創造性轉化(或說「現代化」)中,文化與野蠻的辯證極端地衝擊了人類的思想和感受能力。由創造性的系譜學來看,理性與不理性(déraison)的關係一旦發生改變,兩者之間的界限開始重整,創造活動亦可關注有哪些界限成為可逾越的,有哪些界限經驗在現有的理性結構中成為可能。
傅柯在〈何謂啟蒙?〉中所描繪的「批判」是相應的一種雙重活動。一方面對現有的歷史界限進行考古學分析,另一方面則要跨越這些界限,尋找另類生活和思想的可能。這種「批判」的基本結構在傅柯的早期著作《古典時代瘋狂史》已開始出現了。或者說,晚期傅柯的批判概念試圖落實《古典時代瘋狂史》第一版序言所提及的可能:「瘋狂與理性之間的交換」。傅柯強調,這種交換被現代理性所切斷,因此「批判」的意義不應該受限於反擊理性或讚揚某種「反現代性」,而在於進行理性結構與域外力量之間的溝通(包含非語言的溝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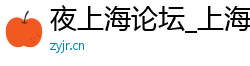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