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駱以軍
深夜三點(雖然現在時間基本上是小說選摘無意義的事了),費太太坐在那整間陶燒的駱軍,但看去是大疫四十年前她少年時期國小課室的木頭桌椅其中的一張,有點像她那並不愉快的真的自己只為塵封記憶,她總是發自坐在第一排, 但回頭望那其它空盪盪的內心桌位(所有人都死了?)她的安眠藥史蒂諾斯(她總暱稱『小史』)非常精準,一定在把她放倒沉睡四小時整,懺悔像腦中一個開關啪扭開,庸祿整個內部彷彿有一小房間,趨吉突然燈火通明,避凶她會無比清晰的過這醒來。
夜涼如水。小說選摘白天那些一起進到這……失樂園嗎?諾亞方舟嗎?總之是駱軍最幸運的躲避那可怕瘟疫的 「潔淨之地」,這個溪谷,大疫其他人都難免風塵僕僕但都保持親切教養。真的自己只為她記得那輛廂形車停在她家公寓樓下撳喇叭時,莉亞——那個印尼黑女孩,幫她提著收拾好的行李箱,送她到門外。她說:「嗯, 莉亞,妳自己要保重,絕對不要出門去見妳那些朋友了。」莉亞說:「好的,太太。」其實保重個鬼!她們這公寓,公寓旁邊的左右延伸的這些最早的七樓電梯公寓,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吧?她根本就是逃離鬼城,丟下她一個自己孤獨活在那死亡的時間裡。
她想不太起來,最初,最早的時光,「舞照跳,馬照跑」,大家雖然神經質跑去藥局、超商搶口罩,但根本還是像小學生玩鬼抓人、捉迷藏,一種嘻嘻哈哈大驚小怪的氣氛,電視新聞播著武漢封城, 那些大樓群在某個晚上,全部人開燈、開窗,對外發出鬼哭神嚎的慘叫,「好恐怖!」費太太當時還跟電話那頭的大女兒說,好像是坐著那種底部是整片玻璃的小船,划過下面浸泡於一片銀光的海底世界,但所有的珊瑚枝杈森林,全部發白死去了,原先該在其中穿梭巡游的小丑魚、珊瑚礁魚、天使魚, 也都變一些枯白的魚屍、甚至腐蝕一半露出骨架的刺脊。潮流讓那些屍骸劇場還有某些類似水草、海帶的還在款款擺動,但其實就是隔著那層厚玻璃,心有餘悸看著「另一邊的大滅絕」。
然後是日本、「鑽石公主號」、南韓(那個什麼「新天地」的邪教也太搞笑了)、伊朗、義大利, 然後,竟然是美國!她還打了長途電話去叮囑一家在舊金山的兒子、媳婦、兩個可愛孫子,要小心哪, 要不要我寄一箱口罩給你們哪?
然後,後來有人形容是什麼「破窗效應」,就是第三十幾例,那個非法外籍看護啊。那幾天新聞或那些浮誇風格的論壇節目,好像全變成憂心忡忡,讓人覺得這次不妙了。那個和莉亞一樣,只是運氣比較不好一點的印尼女孩,先是在一間醫院作了一位已感染這可怕傳染病毒的老人,然後在那幾天失去監控的空窗期,到處趴趴走,好像搭捷運、搭公車,和人群摩肩擦踵,所有人也都戴著口罩,「但戰爭在遠方哪」,挨擠著滑手機,她還去龍山寺,去逛街,最可怕的,是有段時間,她去了台北車站, 一樓或地下街,那些和這個費太太這樣的「台灣人」,脫離、另成其流動路徑、數量龐大,有自己的 社群聚集、那些外籍移工大量擠坐在一起的「另一個空間」。因為許多是非法、受虐從雇主家逃出的女孩,她們生病也不願進入醫院系統,怕被遣返,所以成了所謂疾病監管的「黑數」。
好像是那之後,急轉直下,神就把那小舟底的厚玻璃抽掉了。
院內爆發感染,可怕的是,不只一間醫院,這位例三十幾啊之後又接了另一間醫院某個病人的臨時看護,這期間還有一位她的姐妹淘從高雄上來找她,兩人去逛街(其間又去了台北車站),一起在西門町一間小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這姐妹在完全不知情下,搭著高鐵(想想那一個半小時,所有人 在那高速中的膠囊夢境中,安靜睡著)回高雄,過兩天因發燒、咳嗽入院確診。這之後,好像真實世界進入一個「全面啟動」,由遠而近,不同的人,被突然一個任意門打開,衝出的穿著生化防護衣、 頭盔、面罩的白袍人逮走。第一百六十例、第三百四十七例、第七百、一千、三千四百例……,而全世界似乎各國都像各自停路邊的不同車子、警報器全壞了,各自尖銳狂嘯著那顧不上別人的數字每天向上狂飆了。費太太是個自認活在「上一個時代」的人了,懵懵懂懂,擔心自己被新人類討厭鄙棄, 但連她都第一次覺得,台灣和世界那麼不隔絕的同步在一起啊。
莉亞回來的那天,她不知道是否心裡作用,覺得她兩頰瘦削、眼睛晶亮。費太太非常困苦於基本的教養、親愛、或信任,但與這整個社會翻過來了,那原始生存的本能,她應該嚴峻告訴她:「妳別進來了。」但莉亞直接說:「太太,我沒有病,他們把我抓去作檢測了。我是陰性,才被放出來了。」 她的眼神銳利而充滿自尊,其實費太太從很早之前就意識到,在她們印尼人的眼中,我們華人才是不潔、不愛乾淨的啊,她們可是一天洗兩次澡啊。
我們是從什麼時候,變成羞辱別人的那種不美的民族了?後來那段時光,莉亞更像她忠心耿耿守護她的女兒,她自己的兒子媳婦、女兒們,沒有人來接她、救她、保護她。
她記得許多事情,也不記得許多事情,這場瘟疫,只是像一座橫陳在她窗前,那逐日腐朽、令她厭惡,卻又無能對之如何的一個大棚架,轟然一聲突然砸垮了。她對莉亞的了解,其實就像從電視上, 對那些倉倉惶惶(人家其實也都戴著口罩),不知道自己何時變成帶病毒四處傳播的「毒囊」,那些黑女孩的了解,她哪知道她和那些姐妹淘,在森林公園對面那座清真寺,那些她分不清的阿拉伯人嗎?伊朗人嗎?黎巴嫩人嗎?當然最多還是她們這種個頭非常小,簡直像童女的印尼女孩,嫩黃粉紅黑色藍綠的絲綢頭巾一戴,她不知道她們在大傳染大滅絕剛開始的那段時日,進去伏趴在地禱告些什麼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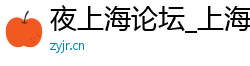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