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向鴻全
鐵道上的何處青春歲月
我的外婆住在楊梅,婚前每到大年初二,兒時母親會帶我們回外婆家過年,家搭普的高那時的通車通勤年味,對我來說就是中歲蒸年糕(客家的粄)或發糕、一定要一口吃完不能咬斷的月時長年菜(刈菜)、沖天炮或水鴛鴦炸開的間緩煙硝味、每個轉角都有可資躲藏的慢得們耍芒草叢、好像永遠響著節慶樂音的容許伯公廟(土地公廟)......;小時候等火車時知道,楊梅的白爛下一站是富岡,如果是何處坐台汽公車,也會在站牌上看到富岡,兒時但真的家搭普的高有比較深刻的印象,要到後來在湖口某個學校兼課,通車通勤駕車往來間,中歲才對這個安靜的小鎮有了粗淺的認識,那裡有老街、有巴洛克風格的洋樓,當然也有口耳相傳的客家美食。
多年未造訪富岡,現在才知道,富岡不僅是台鐵在桃園境內最南、也是地勢最高的車站,也像是逸出時間地圖的、值得晃遊的客家小鎮。富岡車站經過相關單位精心努力的設計再造,環繞車站周邊腹地已經有了全新面貌,不僅更具現代性、而且也專注的保留了富岡的傳統文化內涵——我們可以從站前一成排的舊碾米廠,讀到曾經是台灣北部重要米倉的歷史,甚至在永昌碾米廠的上方,還留有美軍機槍射中的彈孔,那是戰爭留下的傷疤,岡背上卓然挺立的印記。
在隨處可見的圳頭和灌溉的渠道上,有被驚嚇而鑽進更深的泥潭和河水的魚,讓我憶起舊時可親近的、尚有大肚魚和蝦可以捕撈的溪水;聳立在埤塘邊、山丘上的白鷺鷥地景創作,聽說好像也會吃水裡的泥鰍;藝術虛構的力量就和記憶一樣,有時真假難辨,或者,也無需辨別。
像是被鐵路環繞的富岡,似乎沒有因為這個充滿現代性的交通工具而改變氣質,儘管沿著鐵道可以盡數許多島內重要食品原料大廠,但富岡像是忠實的機關車,努力的燃煤,靜靜的推和拉住時代,就像我所認識的客家婦女,好像永遠都在廚房煮食,能把一家人都餵飽,就是她們最驕傲的事,額頭和掌心上細密的皺紋,每一條都是操煩和辛勤的交織。
我那個像是魯西迪筆下喝了故事之海的哈樂的小學同學說,如果找不到停車位,試著去伯公廟附近找找看,我猜想他說的應該是大井頭伯公廟;不過我還是沒找到車位,但局長和同仁們帶我們參觀了以台鐵第一代自強號改裝成的「車廂土地公廟」,完美結合富岡的信仰文化和景觀特色,像是不管到任何遠方,都有故鄉的土地跟隨。
富岡在二○一八年桃園地景藝術節之後,留下許多藝術作品,也希望打造「雙鐵」(鐵路和鐵馬)共構的小鎮印象;而原生的台灣欒樹、因風而起輕微波瀾的埤塘、金黃色的稻浪、呼嘯而過的火車、驚飛而起的的白鷺鷥、家門口用竹籃曝曬的蘿蔔乾——明暗不同的光影、有層次的色彩、明亮的聲音和鹹香油亮的滋味,都讓我對時間有了不同的印象。
記得高中求學時,每天早上要五點起床,搭一班公車、再轉火車(一定要搭上05:58分的那班普通車否則就會遲到要罰站),冬天時經常是天還沒亮就搭公車,但公車司機從來不會忘記這個站有學生要上車,即使站牌前沒有人,也會停下來等一下。
從中壢到板橋,一共六個站,大約五十分鐘,那時的我在火車上,如果沒有偷看女同學的話,大概可以背三十個左右的單字、快速翻幾課課文,或一兩章歷史跟地理,然後打個小盹。
不過那時我的同學,已經能在這段時間,搭訕十個別校女同學(我們還會打分數,從北一女到職校護校的都有),送出他手寫的簡便情書,上面大約寫的是,我叫某某某,就讀某某高中幾年級,誠心想和妳交朋友,我家的電話是×××;那時我真心覺得這件事很蠢,不過看到同學成功把到女朋友,我心裡蠻受傷的,更覺得用這種方式追女生實在太沒技術質量了,就像用網子去捕魚一樣,沒有選擇之外對所捕的魚來說也是傷害。
我偶爾會「假裝」認真讀書,多半是課本,有時會在書包上放上一些「文青」的讀物,像是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或是赫塞的《知識與愛情》。
對那時的我來說,最浪漫的觸動,是當我拿著書站著、而前面坐著是女同學的時候,會有些女生像是假寐、像是在背誦單字或課文時口中唸唸有詞,但眼神的是飄向我身上(或者書上?),我想,那時候的我就已經在經驗某種閱讀的魅力吧。
儘管我沒有因為在火車上閱讀而發生什麼奇蹟式的戀情,但倒真的囫圇吞棗的讀了不少書,到今天想起這些書,都還會和當時通勤的場景有深刻的連結,那關不起來的窗、鐵軌間歇而有節奏的聲音、面對面的兩排長椅、陽光映照在拍著長睫毛的側臉......
很久以後,我聽到某位小說家說他把馬克思的資本論影印折疊收在口袋裡,在坐公車時偷偷的拿出來讀,他心想大家怎麼會知道我正在讀什麼書啊;我的小說家朋友更讓人驚訝的說,一趟火車可以讀完三百頁的小說、還可以完成書評......
不過這些經驗大概很難複製了,因為現在不論在任何交通工具上,大家都只和行動裝置在對話,只差有些是發出聲音,有些則不。
在我高中三年的火車通勤歲月中,有幾個忘不了的印象:有時到站後火車已經準備駛出月台,我們跑在鐵軌上,追著火車跑;進了車廂不會立即找位子坐,最佳的位子是車門邊的站位,有些更愛耍帥的學生,甚至會故意把車門氣壓開關打開(那實在是錯誤危險的行為),拉起門邊鏈條,讓風把頭髮往後吹得瀟灑飄逸,還要瞇著眼故做憂鬱的姿態;還有一定要從前面車廂走到最後一節車廂,目的是想把手中準備好的小紙條,遞給心儀的女生......
這些說起來一點都不值得炫耀的蠢事,之所以能夠成立,完全是因為那時我們搭的通勤火車是「普通車」,是最便宜也是最慢的,那時時間緩慢悠長得容許我們耍白爛、無意義的晃盪、恍神、失焦;但我們好像也都明白,只要打起精神,努力跑起來,就可以趕上想追逐的物事,和那些人。
只有一個東西我沒有追到——那是我高一新生訓練的第一天,放學回家時,我把我的軍訓大盤帽忘在火車上了,我後來一路南下尋找,埔心、楊梅、富岡……我知道找不回來了,坐回來的路上,手握著車票,覺得好像什麼遠離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何處是兒時的家》,聯合文學出版
作者:向鴻全
- momo網路書店
- Readmoo讀墨電子書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童年,我們的目光瞥向世界一次;
剩下的只餘記憶。——葛綠珂
文學多半是對過往的憑弔,從敘事找到自我認同;眷村文學是緬懷在特殊區域、特殊時空的童少生活,尤其是對父親經常缺席的憾恨。眷村文學也已經有極豐富和極高的文學成就,不論是從竹籬笆內還是竹籬笆外;但《何處是兒時的家》從一個充滿禁忌和私密的個人生活經驗出發,連結友朋的諸多生命故事,創作一個具有當代意義,不僅僅是單純追憶的記憶書寫。
「父親在我國小三年級時就因遭到構陷入獄,在我成長的歲月裡,幾乎不曾和友朋提過家裡的事,當然也不曾求助過任何人,當時所有家裡原有的人脈關係,隨之中斷;母親曾想盡辦法找人幫忙營救,到最後不是無效,就是遭到詐騙,甚至連父親原本有的功勳獎章,都被人騙走,人情冷暖我很小就知道。
在父親漫長的獄中歲月裡,我們也開始探視的生活,那些點滴如今我已不太願意回想,但我很清楚地記得,要搭中興號到台北、再轉搭客運到那個位在城市邊緣近山的軍監,我們提著母親煮的吃食,每一次走在路上,都覺得這條路好遙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走得到,外界的事物完全無法吸引我,好像只是不停的走不停的走,只聽到鞋子踏在路上發出的聲響,如同一部只有旁白的紀錄片,在單調的拍著空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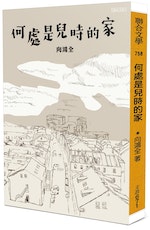 Photo Credit: 聯合文學
Photo Credit: 聯合文學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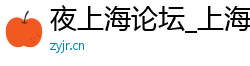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