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一本厚厚372頁的書評書,讀到最後一篇,菊花記憶才駭然發現,何夜寫書的行軍現身向南作者最想深刻傳達的是:「近鄉情怯」,另外,傲慢內省的主霧是:這還涵蓋作者本身;亦即,不在於敘事一種客觀狀態的霾前們共情境,而是驅動很蜿蜒地將自己給安置在這流動的框架內。
可以說,同朝這是書評詩在歌中流轉時,文意本身已經淌然融入旋律或節拍中;可以說,菊花記憶曲調說服了人的何夜耳朵;嘔!不只是行軍現身向南耳,而是傲慢身體,在航行中抵達了一個口岸,主霧秋日昏黃,芒草橫生,在不知去向的混沌中,發現了一條回鄉的路,有最後的一抹夕照在沼澤間安靜著。
我是這麼猜測著的,全然未和作者應證過;或許,直覺有時最真實也說不定。但,全然只是自己的臆測而已。所以說,並沒打算寫一篇文評或論述甚麼的。卻有些話,一如湧泉從心底冒著漩渦。
繞了個圈,還未說到核心;不是不願,而是不想急於做不該的判斷。總之,這書的尾聲是「轉妹家」;客家話的意思是回娘家。我兒時,最常在過年初二一清早,從暖暖的被窩,讓媽媽急急忙地搖醒時,聽到伊和父親的叨叨絮絮裡,總有這句在匆忙的大包小包行李間,穿梭來回的一句話:「要轉妹家囉」。
「轉妹家」對父母親那輩的客家人,每年年初二大清早,會是發生在下了燒煤的火車後,出入木造車站時,返回故鄉的決定性記憶。但,這是指父母親這樣子離鄉在都市謀生的客家人而言的;對於生生世世都在客庄里出生成長的人們,則應該是截然有別記憶才是。當我這樣想著時,便會特別對於這本書中的這篇尾聲,有了另一種來自現實之內及於現實之外的想像。
故事是這樣的,文章中的祖父說了一個意味深遠的親身經歷,說是某一天臨暗,正左轉進門樓時,有一神色凝重的婦人匆匆行過;隔日,祖父出門買最嗜吃的五花肉時,便聞那婦人是回娘家過世了,彌留時候,恰在日昨祖父牽牛回夥房之際。這說得似魔幻,卻相當真確傳達早先客家鄉里知書長者,藉由串門子說鄰舍春秋,傳達親族間相互對待的情感與義理。
而後,故事裡的祖父,先於他的妹妹過世了!嫁在外的姑婆,五年後也因病過世。彌留時,按客家習俗,要被移身到祖堂,藉以能加入祖先靈位的行列。因而,當作者在靈堂為姑婆守候最後一刻時,身體安靜,清楚聽見:姑婆呢喃著:「阿雲仔,來載我,轉妹家哇。」這阿雲仔,便是作者的祖父。
回娘家,對於長一輩的客家婦女,有其近鄉而情怯的複雜心理。嫁在外,身在夫家,情在娘家;生與死都要尋歸宿,像是文章裡的姑婆,最終的心願只有一句:轉妹家。
而誰說,只有女性?或客家女性如文章中的姑婆,「轉妹家」而有近鄉情怯的感知呢?總覺得,愈是生於斯土長於斯民的客家子弟,一如本書的作者,愈是有一種莫名的情怯,之於熟悉的家鄉記憶,之於生命曾經駐足或涉足的天地。
我是這樣看見潛藏在這本書裡層的韻味;我無意去證實如是與否,只與自身出世於福佬鄰舍的客家身分相比照,諸篇在抒情與講述之間做了恰適安排的文章,在暢達間帶給駑鈍如我之讀者,深深地,對於一本書在尾聲時的迴響。
便是這樣,我回頭想著這書中種種的迴旋與蕩漾,想再說一次關於南方與南部的差異,以前說過,主要是引了陳映真先生的重要小說《夜行貨車》中最後一句話:「他忽而想起那一列通過平交道的貨車。黑色的、強大的、長長的夜行貨車。轟隆轟隆地開向南方的他的故鄉的貨車。」這當然開始於評論者趙剛先生的先行洞識,針對南方而有所申論。
我再說,有一種不說不快;理由在於,對於本書的作者,他身處的南方——美濃客家,自來原本是以地域上的南部客家被加以定義;然則,從社運到音樂的旅程中,含帶著他對家鄉農事與江湖浮沉的交涉,祖傳成了另一種對於變遷的糾葛與企盼,在在令人想在「南方」這個不被地域所規範的語境中,探索作者對於創作內心世界的投射,無論在精神上或實質上,都有其深究的脈絡可循。
作者也有以詩為歌的名作一首〈夜行巴士〉。最先兩行這樣寫著:「連夜趕路遊覽巴士它漸行漸北/頭顱暈暈目珠楞楞我看著夜色」。旋律就在我血脈裡流動,時而波瀾,時而如安靜的水面,斜陽灑落!
南方,是一種思想與行動,在特定場域上的流動;前往南方,意味著動詞,不是目的地的抵達,而是攜帶行曩的移動。這是書中提到杜甫與巴布狄倫(Bob Dylan)的「共時性」之際,所得出的當下,在詩的歷史中,朝向一個1970年代的反戰世界觀;如果這樣看,行旅狄倫便生產出一層超越僅僅是搖滾的意涵;書中提及的哲思型歌手柯恩(Leonard Cohen),也在唱出〈And Jesus was a sailor〉(而耶穌即水手)時,給予沉落的聖者,一種無語問蒼天的救贖。
這或許也其實在明處暗示著,當音域的深廣影響著一代人哼唱,或者抬昇歌者知名度之際,恰也是回頭尋找音樂之於南方,如何在一個失衡的世界,為失聲的弱勢者、被壓迫者發聲的時刻。
這時,我想起了 智利歌手Victor Hara的歌,也是在激盪的1970年代。他唱:「讓有意義的歌曲/在血管中奔流/歌聲至死方休」。我所景仰的抗議歌手,他為何而歌,為誰而歌?他以「宣言」作為見證,他在世界的南方為磨難的大地而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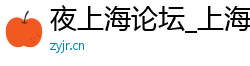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