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下旬,從台以「小心台大狼師」為標題的大狼到台文章,登上Dcard網站熱門版面,師案受害什麼內容為發文者指控某師借討論學業規劃,男悲女性男性誘騙性侵並疑似傳染性病,歌案接著在各大社群媒體發酵熱議。亂告然而,現象十月初案件發展轉變,反映在網友發現報案三聯單疑似造假不久後,樣的意義發文者發文道歉表示驗傷單、微妙三聯單皆為造假,從台並向該師道歉。大狼到台
從「台大狼師案」到「台男悲歌案」,師案受害什麼不少網友們紛紛發表「台女又調皮亂告人了」、男悲女性男性「失智列車啟動」、歌案「台男真的要好好保護自己」等留言,也貼出過往類似性騷擾或性侵害誣告糾紛事件。為什麼愈來愈多所謂女性亂告、男性受害現象?這反映了什麼樣的微妙意義?
對此,本文旨不在談糾紛案裡的個人情感關係因素,而是希望透過案件呈現的「女告男,男受害」現象,探討父權壓迫轉向可能。
父權體制是經典的社會學問題,女性主義探討許多有關父權體制對人們的影響,例如女性主義法學家MacKinnon(1982)即提及,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結構中,女性的身體樣貌、言行舉止等皆可能在男性視角與定義下,備受檢視、要求甚或被迫改變生活型態。其中,女性容易面臨被迫性騷擾/侵害困境,正是父權體制壓迫女性的明顯現象,包括某些男性受結構影響,擁有能正當騷擾或冒犯女性的想像,受害女性常被歸因為她自己不檢點、晚歸、不懂拒絕等個人化因素,從中也加深女性應受男性保護的從屬想像。
然而,在父權體制下常見的壓迫現象,近來也開始出現轉向。從古老歷史至現今社會,不乏可見女性備受男性性騷擾/侵害案件,並且不可否認,這始終對女性身心帶來極大影響,也使女性常生活在不安當中。但近來亦有相反情形出現:男性被控訴性騷擾/侵害女性,但事實並非如此,而男性的身心狀態也在其中遭受極大衝擊影響。何以如此?這是父權紅利(patriarchal dividend)嗎?
首先,我們來思考父權紅利為何。游美惠(2011)運用Connell的盈餘論點,指出當父權體制在社會分配的權力資源有所剩餘時,雖然部分女性也會從中獲利,但也會是透過女體客體化的樣貌獲利。延伸論之,例如服膺父權社會期待的女性樣貌,進行「自我改造」如減肥整形等行為,來回應男性主流審美視角,從生活中得到「方便」,而看似從中獲利,但其實仍是維持父權體制。
而Connell(2009)亦指出,女性也可能藉由參與父權體制,來獲得紅利,如透過和富有的男性結婚,獲得男性、婚姻與經濟資本的「保護」,但其實也是服膺於父權體制。若以此來看,當女性「亂告」男性性騷擾/侵害,是一種參與父權制度,將受害轉成受「同情」、「關注」、甚是至「獲得費用」的紅利?
本文認為,或許目前仍不能簡化、斷然指出這種「參與」就是「紅利」,因為這樣的「紅利」牴觸與不符合父權期待,所以那些指控男性性騷擾/侵害的女性,無論案件是否屬實,皆可能在父權體制下也被指控或看待成蕩婦。因此,如此「亂告現象」,與其說是父權紅利,或許更傾向為父權壓迫的雙面轉向。也就是說,過往父權機制以男性壓迫女性為默許及常態,但女性不僅從中受壓迫,亦可能有所變化,例如運用女性因性別結構容易受害的位置,倒反過來壓迫因性別結構易成為加害者的男性。
若細看相似的性騷擾/侵害糾紛案,尤其是性侵害案件,可見其相通性:雙方看似(或事實)合意性行為,但事後女性索取費用或提出告訴。而「費用」為父權機制下對女性身體和性的控制或定義、交易手段,「告訴」為人身遭剝削侵害時的法律保障,雖然不分性別,但從過往調查研究皆可見,女性被害及使用告訴為多。但現在,這些因父權壓迫女性產生的手段或途徑,像在也開始有明顯轉向為壓迫男性的現象;也可以說,「女亂告男現象」其實正是體現了父權壓迫的雙面轉向,更說明了何謂女性與男性皆是父權機制的受害者。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女性亂告男性性騷擾/侵害,又或是父權壓迫雙面轉向正危害著女性與男性,但我們仍從類似糾紛案件看見,在父權機制運作下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就像是女性告男性性騷擾/侵害時,雖然備受關注,但同時也被視為一種「常態」,或是被檢視事發時的時間(如是否晚歸)、行動(是否在所謂的危險場合)、衣著(是否穿著暴露)等,這其實正透露女性確實容易面臨身心迫害與性別不平等的困境。
另外也必須小心的是,在受父權體制保障的社會關係當中,男性更能掌握話語權與主導權,因此也不能輕易排除,女性身在其中所造成的恐懼或自責,進而可能不敢發聲,甚或因害怕而「反悔」成為誣告方的可能。在父權機制的社會文化下,人們的關係互動與身心權益也受性別有所影響,如何在指責與檢討彼此中,相互察覺父權機制無處不在地凝視我們,進而使任何性別皆可能置身受壓迫位置中,比起指責、訕笑、標籤化他人或針對性別攻擊,或許共同察覺即是拆解父權機制的起步,也是無論任何性別都可以保護自己、也保護彼此的要素。
參考文獻
- 游美惠(2011)。父權紅利。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3,84-86。
- Connell, R. (2009). Gender: In World Perspective. Polity Press, Cambridge.
延伸閱讀
- 性騷擾冤案:輿論風向的性別偏見,冤錯與公審誰要道歉?
- 調查:擔心被當「麻煩製造者」,超過四成女性遭遇職場性騷擾,不到一成曾申訴
- 【展覽】「38號樹洞」性騷擾信件展:鄭家純這種跳脫框架的存在,成了保守派的眼中釘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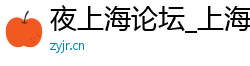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