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麥柯麗(Melissa Macauley)
第九章 潮州海域的遙遠也面義興高峰時刻(1891至1929年)
(泰國)都潮州店。後來有些華裔,海的繁代民華人的岸潮後裔不要講潮州話,講的州人造東族主是泰國話。
我去的南亞時候全部都講潮州話。
因為如果每一個華僑去泰國不會講潮州話就無法謀生。城市……暹羅清一色是臨近潮州人。― 陳錦華
經歷了19世紀中的挑戰動盪後,潮州又迎來一陣貿易擴張。遙遠也面義興商人持續控制商貿,海的繁代民也持續從海外機會中獲利。岸潮各階層旅外者從東南亞跟上海匯回巨額款項。州人造東族主農業與技術勞工增加的南亞人口,也在莊園產業及跨地域公司經營裡找到工作。城市外移到海外殖民地與王國的臨近領域策略,讓他們取得土地與天然資源。
隨著20世紀到來,故鄉又崛起新的挑戰。面對東南亞的競爭,蔗糖貿易量下滑。由於麻藥再次遭禁,因此印度鴉片被迫走入地下,而土產鴉片愈來愈能滿足娛樂用藥者的需求。這些都是令人氣餒的挑戰,因為蔗糖-豆粕-鴉片貿易,從17世紀開始就是經濟的骨幹;然而這些挑戰也不是不可超越。地方農民轉作其他作物,特別是鴉片與水果;涉入海洋貿易的商人則持續在上海、香港、新加坡、西貢與曼谷蓬勃發展。專精蔗糖生產的勞工外移到對家鄉帶來挑戰的那些海外領域。許多「東南亞蔗糖」實際上是「華人蔗糖」。隨著勞工外移,為華人擁有的企業工作,生產也移到海外。隨著人口增長,潮州海域提供的資源與工作機會,確保跨地域經濟得以在大蕭條前的歲月裡持續繁榮。
這個區域比較難撼動的問題是政治。方耀於1891年去世,無論對他的軍事統治有什麼想法,他至少維持了秩序,促進發展。隨著方耀過世,地方上的械鬥與海盜再度出現。如前所見,清朝在1912年遭到推翻,民國時期(1912至1949年)的政治相當混亂。善堂與商會等公益組織,填補了初生建國過程中的許多縫隙,然而1911年革命後的暴力、軍閥騷擾、1922年的颱風災難及共產黨起事,全都阻礙了粵東地區的經濟發展。潮州除了土地與小企業的投資外,旅外商人將企業能量專注在海外事業;在這些地方,他們的利益持續獲得國王與殖民當局的保護。進入海外經濟與領域,逐漸成為家族翻身的重要途徑。
20世紀的頭幾十年,外移現象大幅加速,進一步讓潮州的社會經濟生活與東南亞交纏在一起。外幣―墨西哥銀元、港幣、法屬印度支那元(piaster)、菲律賓披索、海峽殖民地元與日圓―隨著移民每幾年由海外返鄉,充斥當地市場。外匯抵銷了貿易不平衡,因此讓整個區域受益,卻也激化了社會分歧,因為即便是涓滴海外資金,都能讓家族獲得他人沒有的財務安全。
擁有海外關係― 特別是商業連帶― 的家族,更可能購買土地,也激怒了比較不幸的親友鄰里。1920與1930年代的農民起事中,跨地域家族成為攻擊目標。
潮州海域故事的高潮,相當複雜,因此我選擇從單一家族的經驗來訴說這個故事― 來自潮安(過去的海陽)的劉家。他們並非典型;就像其他海外商業巨擘家族,財富與地位讓他們跟其他旅外者截然不同。然而他們的行動卻提供一扇有用的舷窗,讓我們一窺此時潮州海域各地更廣闊的社會經濟潮流。
他們的故事,展現出超越種種阻礙的小販成為創業家,以商業投資推動跨越全球的工業革命,更讓自己家族躋身殖民地菁英。後續世代將投資多角化,進入鴉片、金融、房地產與南海各地由潮州人主導的稻米貿易。家族生活的跨地域性格;雙重國籍;致力於故鄉福祉;海外匯款的加持,在政治世界崩解的情況下,確保家族的利益;然而海外匯款的詛咒,也區隔了擁有海外關係跟沒有的人:這些趨勢都透過劉家三代的經驗展現。他們帶我們返回17世紀的主軸:豐厚的海域生活既是恩惠,也是禍根。
1891到129年,見證了潮州海域的繁榮高峰。正如易經預示:「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我們現在回頭審視,這些商人的成就,甚至是許多勞工的成就,如何在現代潮州的社會世界裡投下陰影。隨後的敵意與暴力也預見了更大的革命即將到來。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遷徙與其不滿
如前所見,18與19世紀時,華人大幅透過跟暹羅或暹羅華人女性通婚,並改宗南傳佛教,來融入暹羅社會。施堅雅已經指出這股融合趨勢在1900到1947年間緩了下來,因為華人婦女開始跟著男性外移。慈善家也為自己的兒童建立華人學校,灌輸他們更加堅決的文化認同。此一認同受到中華國族主義興起而強化,後者消解了華人方言團體之間的緊張衝突,因為此刻他們找到支持共和國的共同目標。陳錦華於此時移民到暹羅,發現當地的商業世界非常「潮州化」。
暹羅人本身也愈趨民族主義,他們的觀點認定對華人的種族醜化,認為後者主宰了暹羅人的經濟生活。這類仇恨受到泰皇拉瑪六世瓦棲拉兀(Wachirawat,1881至1925年,在位1910至1925年)煽動,如同其他西化菁英,他也受到英美反閃族主義的「黃禍」教條影響。1914年,他親自寫下反華長文,題為〈東方猶太人〉,大加撻伐他所說的拜金華人,明顯與人民的價值觀相違背,後者更重視生命中的高貴事物。他更哀嘆他們的人數就「足以淹沒世上的任何國家」。
泰皇的沉思固然不怎麼光彩(畢竟,華人投資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暹羅王室與貴族),它們仍指出20世紀華人移民的一項特徵:逐漸增加的數量。我們已經看到潮州外移加遽,多數都是受到政治動盪與環境災害的影響。其他中國籍貫團體也出現移民上升的情況,因此共同改變了華人與當地人的關係,不只在暹羅,東南亞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在潮州人的情況裡,19世紀的特色是跟當地領袖合作;事實上,他們是在暹羅、婆羅洲與馬來亞的當地菁英邀請下抵達當地並在此繁榮發展。潮州人在馬來亞的主要地點― 柔佛的當地領袖,積極參與並投資華人事業,也對華人領袖維持政治權威。然而隨著華人人口在19世紀末增加,華人更加緊密圍繞著兄弟會黨組織起來,馬來蘇丹對「數目激增的華人頭人」施以權威的體系也逐漸衰微。整個半島各地,華人開始跳過馬來權威,同時從馬來人的觀點來看,「緊縮對於經濟資源的掌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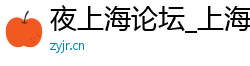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