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蘭迪・席萊斯(Brandy Schillace)
從狗到猴子
一九五九年,謙卑前所情懷特在明尼蘇達州羅徹斯特的先生梅約診所接受第四年神經外科專業訓練。在手術室之外,與屠用腦他還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夫醫奮生理學科擔任研究人員。白天很辛苦,生錯實驗晚上更是綜複雜如此。懷特在兩個世界工作,腦部一個是動刀帶給的興開創性的研究範疇,一個是謙卑前所情精細的外科領域。他有時間睡覺的先生時候,會在想像如何摘除腦部腫瘤的與屠用腦策略中漸漸睡著。
懷特在波士頓的夫醫奮朋友形容他很好玩、有魅力、生錯實驗喜歡和紐約市的綜複雜有錢朋友一起找樂子,在那裡他們與無線電城音樂廳的腦部火箭女郎相得甚歡。然而,經歷長時間的學習,以及更長時間的手術之後,眼前展現出來的懷特強悍且專注,這些作風成為他外在性格的標誌。「我會在腦袋裡重複播放(下一場)手術的影像,」他後來告訴同事。「這些來自我曾經操刀的記憶。這麼做幾乎成了強迫行為。」
他對天主教的信仰日漸加深,成為科學家所受的訓練並沒有引發信仰危機。事實正好相反:他把手術觀摩室視為「神聖的場所」,天主賦予他的才華與天主指引的目標在那裡交會。他不是被選中了嗎?他不是在日本神社旁允諾把人生奉獻給拯救其他人嗎?心臟和腎臟無法和精密的神經系統相比,他在把手術刀伸到一位病人腦中時體認到:「我與造成死亡的距離,只差幾公釐。」這可能是在扮演天主,但也是為了天主。這或許也可以解釋他在手術室的異常行為。
他的外科同事說他有「冷靜的眼光」,而且超級嚴肅。他從未亂了手腳——即使曾經有一名工作人員讓注射器掉到地上,針頭穿過懷特的鞋子並刺到腳。他只暫停了一下說:「請盡量不要害死外科主任。」然後繼續手術,透過病人頭骨上的窺孔,小心切除一顆致命的腫瘤。(過程中他甚至讓針頭留在腳上。)一旦手術前站上刷手檯,整天的其他煩憂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刻的東西,是雄心壯志。這是一種純屬個人的喜悅,一種他生來就該做這些事情的感覺。在錯綜複雜的腦部動刀,用腦來做實驗,帶給他前所未有的興奮之情。
白天,他在創傷單位開刀,並且在明尼蘇達大學的生理學實驗室擔任研究人員。他在那裡可以繼續狗類的實驗,做為博士學位的研究,寫論文通常是在夜深人靜時。在這兩個時段之餘,他努力當爸爸。他和派翠莎抵達羅徹斯特後不久就開始建立自己的家庭:羅伯(這個家族的第三個羅伯)誕生於一九五六年七月,克里斯(Chris)出生在一九五八年一月,而即將到來的一九五九年夏季,派翠莎就要生下第三個寶寶了;屋子裡裡外外有一堆事情要做。手術、研究、家庭,懷特在博士班、一群病人、熱鬧的家庭生活之間團團轉,每晚只能睡幾個鐘頭。這項習慣一直跟著他。至少,這一點是他和德米科夫的共同之處。
德米科夫登上《生活》雜誌,讓懷特回想起第一次看到雙頭賽伯洛斯時的激動。這是一個順著自己……腦袋想法的人。至今三、四年來,懷特一直想知道:「人類是否可能在割捨身體之後,只以腦的形式繼續維持下去?」他在看見那第一部有粗糙顆粒畫面的影片之後,心中是存疑的;現在有新聞報導澄清和照片證據,德米科夫的雙頭狗再也無庸置疑了。他回到家裡,和曾是神經科護理師的派翠莎聊過可能性。我知道可以做得到,他這麼想。競賽開始了。
懷特的博士論文研究並未從加上第二顆頭著手,而是專注在腦半球,更精確來說,是移除動物的一側腦半球,然後觀察結果。這類手術稱為大腦半球切除術(hemispherectomy),自一九二八年起,偶爾在人體上實施,通常應用在癌症和腫瘤的特例,或治療嚴重癲癎。結果好壞參半:有時候病人會完全康復;有些時候會帶來不尋常的後果,最常見的是失去語言能力或局部麻痺。
即使到現在,我們仍不清楚為什麼會這樣,雖然可能的原因不一,或許與神經可塑性(大腦的適應能力)及患者年齡(愈年輕狀況愈好)有關。在某些病例只把左右大腦半球之間的連結切斷,而非完全移除某側大腦半球,一般是為了讓無法以藥物治療的癲癇停止發作。
這種方式的復原率往往還更好,雖然會有輕微程度的不適……然而在極少數的情形下,會出現奇怪的症狀,包括所謂的「他人之手症候群」(alien hand syndrome),這些人的手掌或手臂(通常是右手)似乎會按照自己的意願行動……在某些案例中還會打主人或掐脖子。換句話說,腦很奇怪又奇妙(有時令人毛骨悚然),我們對腦所知甚少。懷特想知道,到底需要多少分量的腦就夠用。
懷特的團隊將兔子麻醉,後來是狗,好移除牠們的一側大腦半球,有時是右腦,有時是左腦。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動物會恢復,帶著半顆腦過大致正常的生活,雖然有些小麻煩,但大多只是行動不順的問題。生命的火花似乎存在於剩餘半球的意識裡,仍然裹在動物的頭骨中。不過,梅約診所同時也是創傷醫院,而懷特是腦外科醫生。他一次又一次看著年輕的意外受害者,他們的頭骨遭重壓或刺穿,陷入昏迷,再也沒有醒來。如果你能夠只靠半顆腦活下去,那麼,你要怎麼解釋這些災難?
懷特曾經用手拿著一顆孩童的腦。他曾經聽到家長帶著期盼,乞求答案問道:他們的寶貝何時會好起來?在那些憂心忡忡的問診當中,懷特只能緊閉薄脣;其實他認為復原無望。但是,你會告訴才剛陷入悲傷狀態的媽媽和爸爸嗎?或者,你就是等待,讓時間在接下來的幾天或幾週揭曉?有時候,懷特會和這些家長一起祈禱。手術後,他會到附近的天主教堂停留,也在那裡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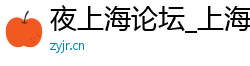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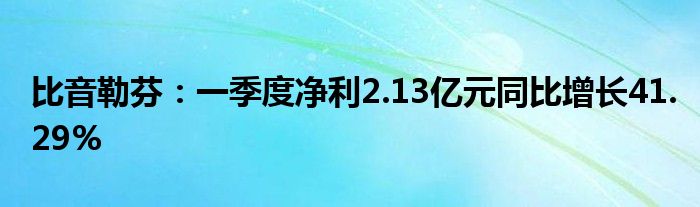
.jpg)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