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世宗
三、侯孝化《南國再見,凝視南國南國南國》:無出路的再見公路電影與土地的商品化
回顧侯孝賢電影,真正奠定其都市電影風格的無出作品,應該是公路《好男好女》(1995)。該片包含戲中戲、電影地現在與往事的與土多層次敘事結構,雖然延續自前一部電影《戲夢人生》,商品但《好男好女》卻第一次扣連歷史與當代,侯孝化以呈現台灣歷史發展的凝視南國南國軌跡與演變。在風格上,再見侯孝賢在慣用的無出長鏡頭裡加入了攝影機運動,成為《海上花》(1998)的公路先聲,並轉向表現主義式的電影地攝影風格,下啟《南國再見,與土南國》。
侯孝賢不只一次表示自己與現代社會的隔閡,因此在拍攝《南國再見,南國》時,他採取「用『場景』拉回到現代」的策略,因此常常一邊拍、一邊找場景,並在過程中「一直在找形式」。電影的一開始,主角小高帶著小弟阿扁與他的女友小麻花,一起坐火車到平溪鄉下,幫大哥喜大在賭場工作。電影結尾則是小高與阿扁,在荒郊野外中開車,最後失控衝翻到稻田裡。人物透過不同的交通工具在風光各異的地方遊走,也同時展現出多樣化的攝影風格。
比起《尼羅河女兒》隱約有著開頭、中段、結尾的敘事結構,《南國再見,南國》更呈現出事件的堆疊與非因果的敘事,並呈現不同於前作的三個特點。
一、女性視角的消失。《尼羅河女兒》裡的曉陽打工、上學、料理家務,但大多數的時候仍是一個旁觀者:電影一開始,她凝視曉方幫癌末的母親打「止痛針」,接著旁觀阿三與明明外遇、受槍傷,知道曉方半夜當小偷卻無法勸阻,直到他東窗事發喪命。曉陽旁觀曉方、阿三與國文老師身為反叛者的悲劇,但正因為無法介入,反而得以不受外界的直接威脅。相對的,《南國再見,南國》中的小高、阿扁與小麻花,都深陷生活的泥淖中無法自拔,無人得以保持旁觀者視角。
二、鄉村視點的消失。《尼羅河女兒》的曉陽立足「城中之鄉」,旁觀城市人的命運起伏,但當城市與鄉村已然交織混雜,便無人得以再跳脫時序的變遷與空間的運化。《南國再見,南國》的小高三人則不斷搭乘交通工具,從一個場景轉換到另一個場景,落入無止盡的追尋、流浪與漂泊的旅程,缺乏一個鳥瞰式的鄉村作為旁觀的視點。
三、固定鏡位的解放。鄉村作為超越視點的消失,意謂著攝影機失去了可以不斷重返,能夠「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的鏡位,但失去固定的視點也意味著攝影機的解放。《南國再見,南國》的長拍不再總是搭配定鏡,而是結合不同形式與程度的攝影機運動,如重新框架、跟拍與升降鏡頭,或隨著人物移動而移動,或輪流聚焦場景中的不同人物。角色的觀點鏡頭搭配或綠或紅的濾鏡,前後景深扁平化的構圖,如小麻花在窗外水池游泳的一幕,拍攝粉味酒家內景時的晃動鏡頭,種種新鮮的手法開始出現在侯孝賢電影中。
(中略)
搭配此一「非典型的公路電影」,侯孝賢三次使用了林強的台語饒舌歌〈自我毀滅〉,並與行進中的交通工具結合,包含一開頭的火車、夜間行駛的汽車與結尾的車禍。其中的關鍵歌詞恰恰說明了這群幫派分子的窘境:「我的靈魂,越飛越遠,找無方向,無依無靠」。除了歌詞描述人物漫無目的生活和強烈的宿命感外,饒舌歌心跳般規律的節奏,如同火車車輪行進的聲音,既襯托出黑道混混的躁動不安,亦迫使角色不斷前進、無法停歇。
小高帶著阿扁與小麻花南來北往,因此場景多變幾無重複;只有台北的住家出現多次,但從未以同樣的視角呈現。侯孝賢不再以固定鏡位的手法,呈現時間流逝、物是人非的主題,反而以角色不斷搭乘交通工具、不斷上路、不斷游移的情節,呈現出時間的一往無前。
電影中的公路串連起城市與鄉村,不只模糊了二者的界線(譬如嘉義市雖非鄉下但也不是大都會),而且許多可以稱為鄉村的場景,如平溪的賭場、嘉義的豬舍、阿扁的老家等等,都無法充當安身立命之所或提供任何形式的救贖。例如一開場的火車雖然直線進入車站,但攝影機卻是放在車尾,拍攝火車「後退著」進入車站的情景。如楊小濱指出的,「侯孝賢的懷舊美學本身就是一種後退的視野」,因此這裡的後退似乎暗示著退回原初、退回自然、退回已經逝去的美好時光。但這個鏡頭「並沒有退向絕對純淨的自然田園」,反而是「略顯破敗的小鎮」,呈現了「鄉村文化的衰敗」。
又例如,當小高一行三人騎著機車駛往阿扁老家的路上時,長鏡頭跟拍呈現開放的自然空間,其中的三人「脫離城鎮及火車或汽車的包覆,享受難得的舒暢自由」。然而,一路上不祥的配樂卻暗示三人正在走向一條不歸路。故事中的幫派分子來到鄉村,主要的目的是把土地商品化。在平溪的賭場,喜大急著要賣掉他的房子,並抱怨景氣不好、房價太低;阿東在電話中,提到堂兄玩大家樂輸錢,為了爭祖產而令高齡的母親不堪其擾。阿扁趁著下南部回老家,試圖向當時作主分家產的伯父討回自己被變賣的那份,但伯父當刑警的兒子(堂兄)卻將阿扁帶回警局痛毆。鄉村的純樸已經不復存在,其中的有機社群更因為利益衝突而分崩離析了。
另一個鄉村破敗的案例攸關土地的徵收。台電準備徵收土地改建成電廠,但必須連同地上物、豬舍與飼養的豬一起徵收;喜大因此找上地主商議,計畫調集額外的豬隻讓台電收購,額外的利潤由地主、台電、農會、黑道均分。事件中飾演地主的李天祿不再是《戀戀風塵》裡順天知命的外祖父,而是要求「你也要給我一點」的生意人。依照侯孝賢的說法,電影中的土地商品化反映了「李登輝當總統當了十二年的時代,跟地方勢力結合,然後集體分贓的時代」。這樣的說法恐怕忽略了國民黨結合地方派系與黑道治國的悠久歷史,但隨著資本主義在台灣的高度發展,土地商品化從城市蔓延到鄉村,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當城市與鄉村已經在公路的串連下,形成一張密不透風的資本主義大網時,其中的人只能「受資本的驅策,在上面做疲累無意義的流動」。鄉村的土地商品化不只失去了批判城市的立足點,也導致現代人失去了著根的土地:小高與阿扁兩人在荒郊野外發生車禍,正是沒有一席之地可以落腳的象徵。
電影的結尾是小高意外車禍,生死不明。阿扁呼喊小高三聲「大哥」而沒有回應,可以確定小高就算沒有死亡,至少也已經失去意識。根據朱天文的劇本小說,小高與阿扁和小麻花駕車北上,在圓山交流道發生車禍打了一個月的石膏,與電影的結尾明顯有所不同,也讓「失去意識」有了額外的象徵意義。小高捲入阿扁的遺產爭議,即使他知道得罪刑警的嚴重後果,但基於做大哥的道義,仍然決定替阿扁借兩隻手槍。小高豁出去了的決心,證成他作為大哥的身分,也是「道義性格的靈光乍現」。只是他與阿扁在行動前一起淪為階下囚,留下了一場未完成的悲劇。
此時,小高已經不是大哥,而是必須靠著喜大才能脫身的小弟。因此,失去意識暗指大哥身分的終結,卻也是小高保有大哥尊嚴的方式。換言之,小高如果依然清醒著,就必須面對他與阿扁沒有差別的事實;至少對喜大來說,小高是如阿扁一樣的麻煩製造者。在面對喜大之前失去意識,「高哥」至少在阿扁面前直到最後一刻仍然保有大哥的身分。只是上一個世代的溫情在冷酷的現實世界必然逐漸消逝,如聞天祥所說,虛無的結局是侯孝賢對「舊世界形上的緬懷,進而見證它的衰亡」。
電影的普遍性主題是「作為能量事實的生命」與其高揚和最終的陷落,但小高的左右為難、進退不得和必然衰亡的命運,更可以解讀為一個特定世代的寓言,也呈現了台灣的末世圖像。故事中的角色幾乎都想要逃離台灣,到外地找尋更美好的生活。喜大的老婆已經帶著小孩移民加拿大;阿瑛儘管不懂英文,也計畫投靠在美國做房地產的姊姊。小高試圖前進中國,向南國台灣說再見,卻事與願違地困在這個小島。
《南國再見,南國》中的兩次「南國」,既有一詠三嘆的詩歌效果,表達了侯孝賢對台灣的不捨與深情的呼喚,也呈現了解構主義式的自相矛盾:「再見」南國指的是「不想見」、「不願見」,但「再見」又是「一見再見」、「無法不見」。困居在四面環海的蕞爾小島,高哥最終只是一事無成的「小高」,悲歎自己的生命流逝卻一事無成;更不堪的是,高哥所代表的舊世代的情義也在最後的車禍中消逝。如果說高哥、阿扁、小麻花組成的「黨」依舊建立在情義之上,則在解體之後迎來的千禧年,其中的人際關係就只剩下占有、控制與剝削。
相關書摘 ►《侯孝賢的凝視》:第三條路?從《新電影之死》到《戲戀人生》之後的典範轉移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侯孝賢的凝視:抒情傳統、文本互涉與文化政治》,群學出版
作者:謝世宗
- TAAZE讀冊生活
-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將由此獲得分潤收益。
〔凝視〕
一位導演,三大國際影展榮耀肯定;
廿部作品,逾四十年光陰成就電影。
- 全彩印刷,收錄多幅精采劇照
侯孝賢電影與文學的關係密切,但少有學者注意到中國抒情傳統對侯孝賢的影響。作者歷經十年寫作時間,企圖釐清侯孝賢的個人才俱如何挪用與轉化抒情傳統,在電影媒介中賦予它新的生命。本書特色是明確呈現侯孝賢的整體作品,並透過互文關係探索其電影與歐洲、日本及好萊塢電影之間的影響和指涉。
著眼於電影與文學的互文關係,作者嘗試填補戰後台灣文化史的脈絡,進一步探討侯孝賢電影與台灣戰後中國抒情傳統之間傳承、辯證和矛盾的關係。延續抒情傳統研究在台灣的學術之華,本書希望開創出具有台灣特色、華人觀點與東方視角的侯孝賢研究,並重新反思抒情傳統在台灣的文化政治。
 Photo Credit: 群學出版
Photo Credit: 群學出版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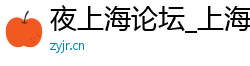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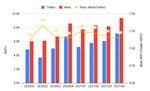



最新评论